在孤独的行走中遇见自己
荣格说:“孤独,并不是身边没有人,而是那些对你来说重要的事物,没有人能够理解。” “人一生的使命,就是走向自性,实现个体化。” 在荣格看来,孤独和痛苦并不是失败,而是灵魂提醒我们:你还没有遇见完整的自己。荣格的话让我想起了Rachel Joyce 的小说《The Unlikely Pilgrimage of Harold Fry》。
小说的主人公Harold (哈罗德)是一位普通的英国退休老人。一天早晨,他意外地收到了二十年未联系的昔日的同事与朋友Queenie (奎妮)的信。她在信中告诉哈罗德,自己身患癌症,正躺在临终关怀医院里等待死亡。哈罗德很难过,他写了一封简短的回信去寄。可是,当他走到邮筒前,却无论如何也无法把手里的信投进去。站在熟悉的街区里,他忽然听见了灵魂的声音:我是谁?这一次,我不能只是写一封信!一个莫名的念头占据了他:只要他不停地走,奎妮的生命也许就能延续。
奎妮曾是哈罗德在酿酒厂的同事,一个寡言却温柔的女人。社恐的哈罗德在人群中总是笨拙、不善言辞,而奎妮却在他的沉默和笨拙中看见他的善良。她会在他尴尬时递上一句体谅的话,也会在他迟钝受伤时伸出援手。哈罗德心里一直深深地感谢她。然而,当叛逆的儿子造成工厂的意外,本该解释的哈罗德却不敢站出来。奎妮看到他的恐惧和无措,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离开了工厂。没有告别没有指责,只是默默地消失在他的生活中。而哈罗德,明明心中十分愧疚,却用几十年的沉默来回避面对此事,表达心中的谢意和歉意。
哈罗德想起了儿子David。那个聪明敏感却始终孤僻的孩子,曾渴望父亲的认可,却一次次失望。作为父亲,他笨拙而沉默,常常在最需要表达时退缩。父子关系长期紧张、疏远。最终,儿子选择了自杀——这是哈罗德一生中最沉重的阴影。直到失去儿子,他才意识到自己的缺席与冷漠是错得多么离谱。他从未能真正伸手拯救自己的孩子,后悔和愧疚反复折磨着他。莫琳责怪自己,也责怪哈罗德,她在悲伤里固执地幻想着儿子依然活着,她和他对话,也和哈罗德的关系降入冰点。
在路上,哈罗德不断被往事追逐。他想起小时候母亲突然离家出走,酗酒的父亲把生活的不如意都撒在他身上。没有人教他怎样去爱去表达,而他更是从小就学会了把委屈和痛苦咽进肚子里。他想起儿子小时候的笑声,想起自己不知道如何和儿子亲近,想起自己在儿子患上抑郁症时逃避,在接到儿子求救信号时退缩。回忆让他痛苦,却也迫使他直面他逃避的过去。失去了,却未曾道歉;想弥补,却再也无法弥补。行走成了他的忏悔,每一步都触及他最痛的伤疤。他的脚一步步磨出血泡,疼痛的不仅是对奎妮的歉疚,更是对儿子的愧悔。
旅途中,他遇到陌生人,有人递给他一杯水,鼓励他继续走下去;有人陪他同行几英里,与他分享自己的故事;甚至一度出现了一群追随者,把他的徒步当作信仰。陪伴总是短暂的,孤独终将回归。而哈罗德知道,孤独才是他徒步中最需要的。因为孤独的徒步,帮助他脱去社会的面具,靠近那个真实而脆弱的自我,成为他与灵魂相遇的方式。真正的同行者,是他内心的声音——那个长期被压抑、被外界角色埋葬的自我。
当哈罗德终于走到奎妮面前时,没有奇迹发生。奎妮依旧虚弱,死亡不可逆转。可是,在路途的汗水与回忆里,他逐渐与过去的自己、与儿子的幽灵、与妻子的冷漠达成了某种和解。他未能弥补一切,却学会了承受、承认与理解。他握着奎妮的手,说出自己一路的经历,说出自己迟到的感谢。看到这样的哈罗德,奎妮落泪了,这已经是最接近救赎的方式。
荣格说,人必须从外界强加的面具中走出来,才能触碰到灵魂的真实,完成个体化。孤独是人生的常态。有的人像哈罗德,被困在“好父母、好员工、好伴侣”的角色里,却在某个契机里突然发现不知道自己是谁。有的人看似朋友众多、生活丰富,但心中最重要的事却从未有人听见。风吹过田野抚过独行的旅人,仿佛灵魂在呼吸;人群的笑声里夹杂着叹息,好似心底无法安放的声音。喧嚣里的孤独者或许也渴望着成为孤独的朝圣者,遇见自己的灵魂。智慧的荣格提醒我们:唯有直面孤独,听见灵魂的低语,放下面具,敢于在孤独中与自己相遇,人才能逐渐走向“个体化”的完整。而当我们愿意迈出这一步时,就已经踏上了那条通往真实与完整的道路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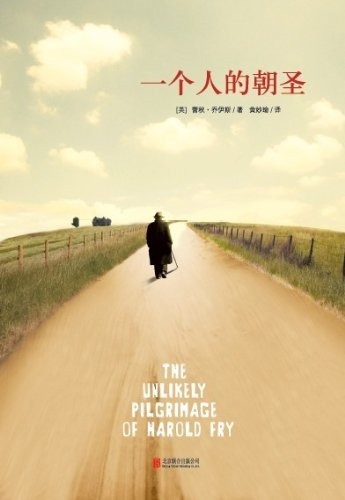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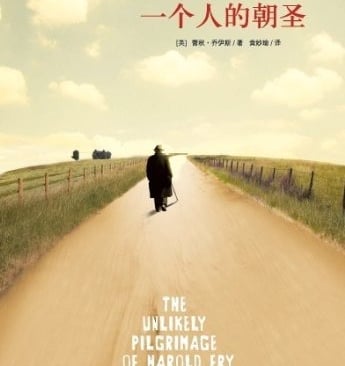
Supporting your journey to emotional well-being.
Chun Lin, AMFT#148396, APCC#17355
Supervision by Lena Axelsson, LMFT#47915